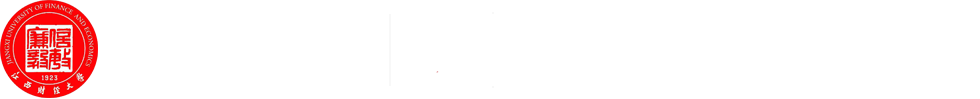中心新闻
中心新闻

6月24日晚,法学院在法体楼Q402会议室成功举办第三十四期“赣江法学讲坛”——“《民法典》规定的遗产信托制度的理解和适用研讨”学术讲座。本次讲座特邀外国法制史研究会副会长、民法研究会常务理事、厦门大学法学院教授徐国栋先生担任主讲嘉宾,由法学院副院长周维德主持。法学院老师蒋岩波、张怡超、熊云辉以及广大学生积极参与本次讲座。

徐国栋教授开篇明义,从遗产信托制度在我国的立法及当前适用出发,阐述了遗产信托制度的起源和发展,论述了我国如何更好适用《民法典》中的遗产信托制度,给广大师生带来了深刻启发。
首先,徐国栋教授讲述了《民法典》第1133条第4款“自然人可以依法设立遗嘱信托”来源于我国2001年颁布的《信托法》有关遗嘱信托的规定,并指出我国立法只规定了其受任人的指定及遗嘱可以为信托的设立文书,遗嘱信托如何运作,需要依靠法律解释来支撑。我国在2019年才产生遗嘱信托第一案,案主采用英国式的遗嘱信托,但采用的不专业,实际上,存在其他的适用遗产信托制度的可能,例如“接力享受遗产型”“二传手型”、“能子继承制型”、“死者作为受益人型”“动物作为受益人型”等。民法法系引入信托法,还存在一些基础理论问题,主要表现为民法法系的所有权概念是否排斥信托法,信托法是否颠覆了民法法系的物权法定主义。上述遗产信托的适用类型存在于历史中,只有通过历史研究的方法才能正确把握和了解。
遗产信托制度起源于罗马法。罗马法上的信托是为了规避法律的禁止性规定产生的,当时的罗马法规定了积极的遗嘱能力和消极的遗嘱能力,前者是订立遗嘱遗留财产给他人的能力,后者是根据他人遗嘱取得遗产的能力,一个有积极遗嘱能力的人若想将遗产遗留给一个不具有消极遗嘱能力的人则为法律所禁止。此时,遗嘱人往往委托自己信任的人取得自己的遗产,再将其转交给法律禁止的不能取得自己遗产的人,此种交易不合法,不被法律保护,能否落实,全靠受托人的信用。经历过各种美谈与恶例后,奥古斯都终于承认了遗产信托制度的合法性,信托实现了法制化。但阿德里亚努斯颁布的各种禁令又使得该项制度变得基本无用。之后,遗产信托制度经历了从“家人遗产信托的崛起”“信托替补制度的起源和发展”“《托罗法》的长子继承制”、“《托罗法》规定死者本人可为遗产信托的受益者”,再到“英国式的遗产信托”以及“美国有脊椎动物作为受益人的荣誉信托”等发展阶段,遗产信托制度变动越来成熟,为广大国家所接受。

纵观我国《民法典》中的遗产信托制度,首先要弄清楚的是其规定的是遗产信托还是遗嘱信托。根据王利明教授团队的民法典草案第620条的规定,其将遗嘱信托的客体理解为遗嘱执行人的工作,徐国栋教授认为由于《民法典》已单独建立遗嘱执行人制度,导致遗嘱信托的表述不确切,所以宜将《民法典》第1133条第4款的遗嘱信托解释为遗产信托。江平教授认为遗嘱信托就是以信托的方式进行遗赠,例如死者将财产交给受托人,由受托人定期交给受益人收益,这实际上是按照英国的路径解释遗嘱信托。受托人取得对信托财产的法定所有权,受益人取得对同一财产的衡平法所有权,后者据此取得信托利益。我国《信托法》起草主要参考了日本的制度,而日本实则采用的是美国的蓝本,用《信托法》中遗嘱信托的含义来适用《民法典》第1133条第4款规定的遗嘱信托,会排斥其余五种在大陆法系国家民法典中或英美法中存活的遗产信托,造成法律资源的损失。所以,在新时代,应该用新的认识来看“老”的制度,不应该《信托法》中的遗嘱信托概念去理解《民法典》规定的遗嘱信托。有关《民法典》第1133条第4款的遗产信托适用方向,杨立新和杨震两位学者认为,我国应该引进德国法中的后位继承即家人遗产信托概念,即遗嘱人可以要求受遗赠人只在一定的期间内享有遗产物,期满后要将它们移交给自己的后手。陈苇认为,该制度可避免继承人或受遗赠人对遗产的挥霍。徐国栋教授认为,我国摆脱独生子女时代后,或许可以在“两户”制度的范围内适用“能子继承制”,此项制度有保留企业性遗产的生产力的积极意义。此外,徐教授认为死者也可以成为遗产信托制度的受益人。《民法典》对动物只字未提是一个遗憾,徐教授主编的《绿色民法典草案》中规定了“遗留给动物确定的财产或确定数目的款项的遗嘱处分有效”,认为可以设立有利于动物的遗产信托。

提问环节,徐国栋教授对老师同学们的疑问逐一解惑,让在场师生感触良多。徐教授的观点振聋发聩,拓宽了师生们的视野,指引了我们今后的研究方向。最后,周维德副院长再次对徐国栋教授的讲学表示感谢,本次讲座圆满结束。